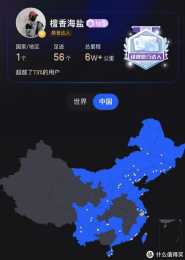首頁 > 運動
燕園往事:在廢園之上重建一座中國園林
由 新京報書評週刊 發表于 運動2023-01-12
簡介對於未來的燕園,一個美國傳教士心目中憧憬的“中國式”校園而言,勺園所在的海淀舊日園林故址近於完美——再沒有比因園造園,“園中園”或“園外園”更順理成章的了
一拓等於多少米

燕大校址上的舊園林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米萬鐘的“勺園”。從皇家廢園到莘莘學子的夢想之地,北京大學校園的前身經歷了怎樣的建造過程?作為中國近代建築史上的關鍵建築師之一,茂飛開創的以清代官式建築造型結合現代技術的“適應性建築”影響深遠。

原文作者丨唐克揚
摘編丨安也

《從廢園到燕園》,唐克揚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1920年11月12日,就在正式購買“滿洲人的地產”的一個多月後,應高厚德之邀,燕京大學校方延請的紐約建築師茂飛和高厚德、斯塔奇博士(Dr。Stuckey)一起踏勘了燕京大學校址。
茂飛和丹納事務所的勘察報告摘要如下:
……地產在北京西北7英里之外,去頤和園的大路邊,從北京使館區驅30分鐘的汽車,由大路,地勢由西向東昇高直至地產東沿,拔起6英尺,這塊地可以很好地轉適於茂飛設計的大學。地產最初是一處滿洲宮殿,和圓明園一同被英國人焚燬——圓明園在東北不到1英里以外。
……整塊地產含有人工小山,水道和島嶼,有溪流由西注入,源頭與玉泉山和頤和園的相同。巨大杉樹和松樹、人工巖穴和石窟加強了此處的自然美,從地產的最高點可以看見周遭的鄉野景色。
總體狀況:遵高厚德先生之囑,我們對地產和附近地方的狀況進行了測繪,也進行了地勢測繪,估計附近建築石頭的數量。因為附近有許多花崗岩石頭,狀況適足滿足建築新房子的需要。地勢測繪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為這對利用地面上不規則性的自然藝術的潛質最有好處,從而可以讓建築師茂飛先生著手安排他的大學建築的群組。
在勘察報告中,附有幾組應紐約託事部要求拍攝的照片,在照片後,茂飛不僅僅描述了每一幀照片中的重要景物,還詳細註明了它們拍攝的方位,以便和測繪圖進行比較。這些珍貴的照片披露了燕園罕為人知的“最初”,在一系列數英寸見方的黑白照片裡,這“最初”沒有繽紛的油彩,只有廣袤單調的鄉野景色,巨大的松樹和小土山點綴在視野裡緩緩展開的一片平疇之中。

茂飛和丹納事務所的勘察報告中所附的照片,今天人們所熟悉的湖光塔影,竟是源自這樣一座廢園之上。
美國風景史學家約翰·B·傑克遜(John B·Jackson)曾經說過,要了解一個場所、一處村莊、一座城鎮如何組織自身的邏輯,最好是回到它的“最初”,回到那只有十來個人、一兩處棲身之所的洪荒之初。
一個最終面積達到兩千餘畝,容納數千學生的現代大學校園,是怎樣在一座四望無人、荊棘叢生的廢園上拔地而起的?
1
燕園歷史:
最早可追溯到米萬鐘的“勺園”
燕大校址上的舊園林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米萬鍾(1570—1628?)的“勺園”。作為萬曆年間著名的書法家,米萬鍾與董其昌、邢侗、張瑞圖並稱“明末四大書家”,更以“南董北米”的盛譽昭示著北方文人領袖的身份。然而,十餘年的南方宦遊經歷似乎對他影響至深,回到北方任職直至去世的近二十年裡,他在北京共留下三處園林勝蹟,三園的營造都多少顯露出他南方生活經驗的印痕。尤其是勺園,在當時的帝都北京素以江南風致聞名,這一點在多種明人筆記中均有記載。
例如,浙江人王思任在《米太僕家傳》中說:“公在海淀作勺園,引水種竹,大似望江南。晚作漫園,領蒹葭之趣。然喜為曲折輾轉之事,門移戶換,客卒不得入,即入也不解何出,客方悶迷,公乃快。”又“米家園、米家童、米家燈、米家石”被列為當時的“四奇”,為時人所津津樂道。
好一個“客方悶迷,公乃快”的江南園林風致——這位喜歡把客人折騰得暈頭轉向的萬鍾先生“曲折輾轉”的情懷,似乎與“北米”的磊落形象略有出入。不過這種“曲折輾轉”,以及對“園、童、燈、石”的並舉與癖好,卻和明末文人生活中的異樣情調契合,隱藏著某種“蒹葭之趣”之外的意味。
勺園究竟如何使得訪者“悶迷”其中?如今只能從《燕都遊覽志》一類的文字中尋覓了:
勺園徑曰風煙裡,入徑亂石磊砢,高柳蔭之。南有陂,陂上橋曰纓雲,集蘇子瞻書。下橋為屏牆,牆上石曰雀浜,勒黃山谷書。折而北為文水陂,跨水有齋曰定舫,舫西高阜題曰松風水月,阜斷為橋曰逶迤梁,主人所自書也。逾梁而北為勺海堂,吳文仲篆。堂前怪石蹲焉,栝子松倚之。其右為曲廊,有屋如舫,曰太乙葉,周遭皆白蓮花也。東南皆竹,有碑曰林於澨。有高樓湧竹林中曰翠葆樓,鄒迪光書。下樓北行為槎枒渡,亦主人自書。又北為水榭,最後一堂,北窗一拓,則稻畦千頃,不復有繚垣焉。
可以想象,從入園起,遊園者的視線便不斷為由亂石、高柳、屏牆、高阜、圍牆、曲廊、蓮花、竹林所組成的各種“障景”所規範和引導,那也便是清初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中所說的“路穹則舟,舟穹則廊,高柳掩之,一望彌際”。
由茂飛的踏勘,我們知道整個燕大校園也不過高差六英尺,即一人身高,從地產的最高點望去,周遭景色本應一覽無餘,但依賴植物配置、人造土山和障牆圍屏,這有限的物理空間卻營造出了逶迤深曲、高低跌宕的江南景緻,與“稻畦千頃”的本地風光截然不同。依據侯仁之先生的考據,結合自燕大教授洪業以來諸位學者的復原推測,我們可以知道《燕都遊覽志》的作者孫國敉所描寫的勺園只是一個不大的狹長區域,但它集中了十所以上的建築和由亂石、湖泊、竹林、蓮花等組成的眾多不同地形地貌的景點。

賴德霖所復原的勺園想象圖(區域性)。
對於未來的燕園,一個美國傳教士心目中憧憬的“中國式”校園而言,勺園所在的海淀舊日園林故址近於完美——再沒有比因園造園,“園中園”或“園外園”更順理成章的了。
然而,我們不應忘記的是,在燕京大學勘察校址時,幾個金髮碧眼的洋人眼中並沒有絲毫四百年前昔日園林的痕跡,真實的景況是,經過米萬鐘身後近四百年的營建和譭棄,勺園早已無跡可尋了,它早已融入一幕“存”與“易”的活劇中,相形於汪洋恣肆的文字與想象,物理現實中所剩下的幾近於零。
20世紀20年代初,人們對前朝的園林勝景還總算有所感受,那便是從“滿洲人的地產”上殘留的地形地貌中,或許還能分辨出一絲古怪的“自然美”——代表著東方式的“不規則藝術”。那些“人工的巖穴和石窟”使茂飛想起的,是他來中國之前,在加利福尼亞州太平洋博覽會上看見的出口外銷的中國風情,還是一百多年前盛行於歐洲的“自然風致”中的人造廢墟?對他此前業已完成的那宏大設計圖景,這“不規則”的自然美又意味著什麼?
在那設計中,齊整的、不考慮地形而普適於一切鄉野基地的建築群組,勢必抹平一切坑坑窪窪、溝溝坎坎,高大的建築體量將使得矮小的假山相形見絀,支離破碎的小湖將不得不被填平,為可以行駛汽車的大路讓道。在這甚少起伏的基地上,若想要呈現英國式的自然風致,本已有些難度;若要進而融合中國式的“不規則藝術”,則是難上加難。
距離清王朝的崩潰不過十年,造園這門行當在中國已經一落千丈。縱然基地上隨處可見廢園裡留下的大石,想再現清代疊山的風采也已不太可能。就像燕京大學後來在調查報告中提及的那般,在集北方皇家園林之大成的北京,他們所能發現的疊石工匠,也只有區區兩個而已,而且這純粹依賴大師心得和個人勞動的手藝,收費之高使人卻步。
這一切茂飛應當想過。
2
是中國園林,
還是“中國式”的校園?
從“廢園”到“燕園”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有跡象表明,茂飛並不視這段路為畏途——他並不像今天的建築師和建築史家們一樣,有著某種難以割捨的“影響的焦慮”。
雖然廢園的歷史淵源顯而易見,但那時候,它們卻未見得對茂飛形成多少實在的羈絆。這位沒來過幾次中國的美國建築師,在此前已經嫻熟地造起四所“中國式”大學了——不管這“中國式”是否真的經得起推敲,重要的是,它們得到了他的主顧的認可。建築師並不總像歷史學家一樣,對史實的準確性懷有一種道德感的牽繫。
對茂飛而言——也對於未來的燕大建設者而言,基地上的“自然”狀況僅僅意味著“唾手可得的建築材料”和影響施工條件的實際因素。至於是否建造一箇中國式的園林環境,恐怕並不在茂飛的優先考量之中,從燕大校方1922年前忙於各種實際事務的狀況判斷,恐怕當時連這個“燕園”的影子都沒有。
中國園林還是“中國式”的校園?是“自然、如畫”還是“因地制宜”?
在各種實際困難糾葛紛亂的“最初”,這些不對稱的組合似乎是風格史中難以開啟的死結,但是,任何選擇都不會是絕對的偶然。廢園所在的基地是江南樣式舊園林的勝地,湖光塔影最終從多種可能性中脫穎而出,這一切並非沒有隱約的脈絡可以索引。這些脈絡並不一定導向昔日園林的歷史影像,卻和另一種“自然”的大勢密切相關。
今天,海淀是號稱“中國矽谷”的中關村和高校區的所在,高樓密佈,商業繁華,和北京中心區幾乎不分軒輊,但數十年前,哪怕三十年前,這幅都市圖景都截然不同——眾所周知,在北京城市突破城牆的束縛、大規模地向外擴張之前,海淀鎮幾乎是北京西北郊,乃至北京郊外,唯一發展為獨立聚落的大規模市鎮,而它的四周均是鄉野農田,和今天車馬如龍的繁華景象截然不同。
在北京西郊的地形圖上,有一條有趣的五十米等高線,它所標示的“巴溝低地”和周圍地形的落差,使得玉泉山—萬泉莊水系不是像北京地區的大多數河流一樣流向東南,而是在這一地區遽然折向東北。河道和泉源的常年流經,將五十米等高線以北的地面侵蝕得越發低窪,水流週轉,便形成了一個半圓形的承水盆地。而緊鄰盆地、不受地勢卑溼之累、地勢高聳的“海淀臺地”,相應成為理想的農業聚落所在。
沿著臺地和溼地邊緣發展的農業墾殖,形成了最早的北京西郊園林的基礎:
海淀正北以及西北一帶,地勢低下,是舊日園林散佈的區域。現在燕京大學西南一隅與海淀北部互相毗連的地方,正是舊日園林中開闢最早的一部分。京頤公路從東南而西北,斜貫海淀鎮的中心。凡是經由這條公路向北來的,一出海澱鎮……即見地形突然下降,如在釜底,田塍錯列,溪流縈迴,頓呈江南氣象。數里以外有萬壽山、玉泉山平地浮起,其後更有西山蜿蜒,如屏如障。南北一鎮之隔,地理景觀,迥然不同。
20世紀早期,人們看到的這些“田塍錯列,溪流縈迴”,具有江南氣象的溼地風貌,同時也是四百年以來米萬鍾們營建“海淀”的結果。海淀,顧名思義,原是大型的內陸湖泊,這一稱呼通行於中古時代的中國。而米萬鐘的勺園及園中“勺海”,也取自“取海水一勺”的語意,當時一片汪洋的景象可以想見。然而從元明兩代開始,由於海淀聚落(大致等於52。5米等高線)的興起,“稻畦千頃”的景象背後是過度墾殖,原先廣闊的湖泊面積顯著減小,形成了一個個大小不等的衍生湖泊,由此產生的地貌倒是與江南地區非常接近。《帝京景物略》有文為證:
水所聚曰澱。高梁橋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滮滮四去,潀潀草木澤之,洞洞磐折以參伍,為十餘奠瀦。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或曰:巴溝水也。水田龜坼,溝塍冊冊,遠樹綠以青青,遠風無聞而有色。
不僅這一帶的自然景象頻繁地被比作江南風光,連地名也帶上了使人遐想的痕跡。
新祠歧路帶前途,十里草生春不孤。
憶我有鄉迷處所,坐看雨氣出西湖。
這些得江山之助的文心畫境,不僅僅是詩人心緒的流露,它們所記錄的經海淀往西山一帶的熙攘客流和田園風光,同時也是北京城市發展的歷史見證。自從女真人的金朝在北京地區第一次建都以來,西北郊的重要就不僅僅體現在它的風光,也體現在自然資源對於都城的戰略意義上。海淀臺地阻斷了西山高聳的地勢向北京的自然降落,不利於城內獲得生活用水,為扭轉玉泉山水系東北流向的趨勢,才有了昆明湖東的堤防和青龍橋的節流水閘,以及在萬壽寺前開鑿、向東南流入北京城的人工水道長河。
3
海淀臺地的北緣:
皇家和庶民的分野
這一“堵”一“分”,便使得古湖泊海淀愈發縮小,不僅風光秀美,而且更便於人居。這樣的形勝之處,歷代的王公貴胄、顯赫之家自當先據要津,西郊園林的開闢從此未曾停止:從明代皇親李偉規模宏大的清華園,直至以虎皮牆圍起整個昆明湖的頤和園(清漪園),從“只取一瓢飲”的米萬鐘的勺園,到“移天縮地在君懷”的“萬園之園”圓明園,不一而足。
這些園居者或訪客自身並不從事農業生產,飲食生活都仰附近聚居的農民就近供給,海淀一帶的農業墾殖由此持續發展,海淀鎮的商業興盛自不必說,有清一代,海淀一直是京西著名的稻米產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的西垣牆外都可以看得見一望無際的水田。
這部分地區的灌溉供水,同時也就是燕京大學新校址內舊園林的水源,萬泉莊水系在此處匯合了昆明湖及長河東瀉之水,繞經燕大和燕大校址西邊的暢春園之間,北流東轉,經圓明園故址南緣,過清華大學北流以入清河。

北大校園內的朗潤園一度有著宛如江南的景緻。作者攝於1997年。
提及北京西郊的歷史地理演進並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試圖闡明這樣一個事實:很大程度上,茂飛在1920年年末所目擊的“自然美”殆非天工,而出自人力。這段人類干預的自然史還有一點值得說明——茂飛或許意識到了,卻可能沒當回事——西郊園林的歷史與西方人在此的“功業”本自密不可分。正如本書開篇所言,近二百年來,由西方影響帶來的野火鳴鏑及現代化程序,一直是北京西郊城市發展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米萬鐘身後約二百年的清乾隆年間(1736—1795),海淀已經為西方人所確知。當時,著名的圓明園業已在燕京大學校址北垣外一箭之地建成,厭煩了城內暑熱的清代諸帝常年在此處理政務,因此帶動了這一地區的空前發展。除了圓明園、綺春園、長春園(此三園或合稱為圓明園)、清漪園、暢春園這些規模龐大的皇家離宮之外,尚有淑春園、弘雅園(集賢院)、鳴鶴園、朗潤園、鏡春園這些後來被時的辦公地點。

20世紀30年代的朗潤園。
直到北四環路修建之前,北京大學附近很多反映這段歷史的地名尚保留著,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一條名叫“軍機處”的小巷,通往海淀鎮上眾多為人們至今回味的飯館。“軍機處”的路面比北京大學南牆外的海淀路高出一米多,除了高度向人們昭示著海淀臺地的邊緣所在,它的名字還再清楚不過地告訴人們,此處正是當年清朝大臣租賃民房辦公的場所,而海淀臺地的北緣,也在當時成了皇家和庶民的分野。
4
海淀鎮的黃金時代,
在圓明園的一炬中灰飛煙滅
米萬鐘的勺園在此時已經改名為“弘雅園”,康雍乾時期,這裡一度成為貴族積哈納(鄭親王)的府邸。因為清代規定皇族賜園不得世襲,受賜者死後園宅必須歸還,1784年之後,弘雅園不再歸私人居住。到了1793年,第一個來華的西方使節,由於“禮儀之爭”而廣為人知的英國人喬治·馬戛爾尼勳爵(Lord George Macartney)被安排在此居住。馬戛爾尼的訪華日記,以及回國後根據這些日記寫成的中國行紀,讓地球那半邊首次知曉了東方帝國虛張聲勢的內裡,也使得燕京大學的校址第一度為西方人所知。
在書中,馬戛爾尼仔細描述了他所居住過的中國園林的情狀:
分撥給我們居住的此地住宅由數個庭院和互不相連的廳堂組成,位於一箇中國樣式的園墅中。園墅中蜿蜒蛇行的小徑和狹窄曲折的河流環抱一個小島,島上有一個涼廳,一叢間錯著草坪的各色樹木,由於不規則而顯得多樣,因大石而具野趣,園子有一道圍牆環繞,門口的一隊士兵負責看守。
值得說明的是,後來燕京大學的歷史學家洪業在他的《勺園圖錄考》中也引用和翻譯了這段文字:
所備為餘等居住者,為數庭院,各有堂廂,共在一園內。園為中國式,曲徑纏繞,小河環流,中成一島,上有涼榭一,草地與雜樹相間錯,高下不齊,頑石亂堆。全園居高垣內,園門有兵守之。房屋中有頗寬敞優雅不陋者。惟久未修理。
洪業的翻譯簡潔文雅,但是它流露出的欣羨語氣,或多或少地埋沒了這段描述所指向的歷史情境。英國人心目中的天然開敞的“園墅”(park),和他們眼前充滿“蜿蜒蛇行(serpetine)的小徑”與“狹窄曲折的河流”的中國“園林”(garden)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兒。事實上,英國使團中的好些人在弘雅園中並不愜意,不管是“蜿蜒蛇行”還是“狹窄曲折”,“不規則”還是“野趣”,這些詞在上下文中都多少有點貶義,和它們象徵著的神秘而陰暗的東方人的心計不謀而合,環繞在園子外的那道圍牆和負責“看守”他們的清朝士兵進一步解釋了一切。
法國前文化部長佩雷菲特生動地描述了弘雅園紛爭的前因後果。雖然馬戛爾尼一行帶來了重要的外交和商貿使命,但在這場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聾子的對話”中,乾隆並不打算以平等的姿態對待這群遠方來客,相反,這群顯然水土不服的洋鬼子面對的是東方最大帝國的君主嫻熟的權謀。他們一會兒被撂在一邊十天半月無人過問,一會兒被拉出去“腐敗”而累個半死,一切都是為了煞煞他們志在必得的囂張氣焰。
眼看著他們長途跋涉快到天子腳下了,這夥人卻就這樣被軟禁在這有圍牆和有衛兵把守的弘雅園中,住地戒備森嚴,和外界完全隔絕:“不管我們用什麼藉口,他們都不讓我們出去。所有通道都派有官員和兵士把守。這座宮殿對我們來說只是一所體面的監獄而已。”
顯然,習慣了“自然風致”的英國人對這樣的園林境界無法欣賞,在這對他們而言並不舒適的囚籠裡牢騷滿腹。這些房子“過去是給外國使節住的;但很明顯,這房早已沒人管了”。“屋子裡到處是蜈蚣、蠍子和蚊子。”“英國人不得不睡他們海上航行時用的吊床和行軍床。”“這個國家老百姓睡的床都很不舒服。”
佩雷菲特確切地說,這是因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英國人毫不留情地揶揄這園子的一切時,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們卻在為他們縝密而不失巧妙的應對暗自得意。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的諭旨稱:將安排英使一行“在弘雅園居住”——這園居在皇帝看來顯然是一種高規格的接待,“英使將看到該看的東西,規定以外的一律不準看:‘……皇帝同意英國貢使乘坐龍舟遊覽昆明湖。湖水必須相當深,你們要派人疏浚昆明湖,務使一切完美無缺’”。“政府對一切都作了精細周密的安排。即使波將金給葉卡捷琳娜二世看的村莊也不比這佈置得更好了。”
這裝門面的遊園會並未如清廷所願,使“英夷”震懾於天朝上國的文物制度,相反,當英國人走近圓明園,看清了裝飾有龍和金色花朵的園牆上原來“工藝粗糙,鍍金的質量很差”,他們原有的憧憬和欣羨便煙消雲散。
四十多年後,英國人首次在南中國海以堅船利炮打掉了這停滯帝國古老的高傲,英國兵艦第一次入侵便行駛到大沽口外,首都北京震動。事隔十多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更是來勢洶洶,雖然對中國而言兩萬人實在算不上一支大軍,但這兩萬人卻在停滯於冷兵器時代的清軍面前佔有絕對優勢,打得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也望風披靡。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聯軍由通州直趨圓明園,繼馬戛爾尼和1816年被驅逐的阿美士德勳爵之後,他們的孫輩額爾金勳爵最終又踏進了圓明園,只不過這一次他是這座“萬園之園”的終結者。

盛期的燕大校園,由今未名湖南岸往西北方向觀望,圖中可見湖心島。
在這之前,弘雅園早在嘉慶六年(1801年)改作漢、滿文職各衙門堂官的公寓,以“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之意改稱“集賢院”。傳說在戰爭期間,園林中那些先前的“國賓館”“公務員宿舍”,轉而成了關押外國戰俘的拘留所,英國談判代表巴夏禮(Harry Parkes)被囚此處,受到了中方的虐待。這後來成了英法聯軍焚燬並洗劫圓明園的藉口之一。據說,在決議燒燬圓明園的前夜,法國人似乎要稍稍剋制一些,而憤憤不平的英國人卻聲稱,在這附近的某一處所,他們的代表受到了酷刑——“被俘之英法人,手足拘縛三日,不給飲食,如此暴行,即在圓明園中為之”——燒燬包括集賢院在內的皇家園林,就是最好的報復。
園毀後不復再建,海淀鎮的黃金時代遂在圓明園的一炬中灰飛煙滅。
饒有意味的是,三百年來,西方人的每一次出現都給西郊的山水園林帶來某種重大的變化:以王致誠、郎世寧為代表的耶穌會士在18世紀幫助乾隆皇帝建起了圓明園中那些模仿路易十四時代作品的“西洋樓”,給它帶來各種珍稀玩意兒和“奇技淫巧”的陳設;馬戛爾尼則揭開了這座園林神秘的面紗,使它置於苛刻而不懷好意的審視下;最終,又一位英國人出現了,給它帶來了滅頂之災。
現在輪到了美國人茂飛,他生活在科學昌明的20世紀,來自業已成為世界超級強國,但才剛剛開始海外擴張的美利堅合眾國。茂飛並不是一個歷史學家,面對著貧窮積弱,甚少人看好,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去理解的古老中國,他將在對這歷史過往幾乎一無所知,或可以說一竅不通的情形下,在廢園之上重建一座嶄新的“中國園林”。
本文節選自《從廢園到燕園》,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
延伸閱讀
(關注書評週刊影片號,觀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劉擎薦讀:《思想家》)